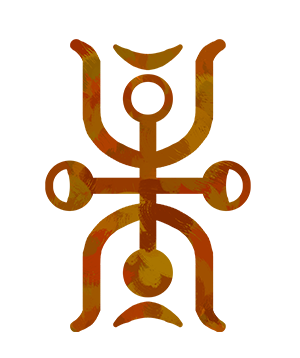塔罗牌手势的密钥
Enrique Enriquez免费分享的读牌方法。
本文于2009年在Enrique的个人博客Tarology中发表(此博客现已关闭多年,无法查看)。
本文先以诗句的形式,描绘了恩里克•恩里克斯自己是如何理解以及启发我们去理解塔罗牌中的“手势语”,然后又对诗句进行逐节解析。
恩里克•恩里克斯曾在他拍摄的纪录片《Tarology》中表达过这些内容,以模仿塔罗牌中的人物角色的姿态去理解纸牌所传达的内涵。
作者:恩里克·恩里克斯,纽约,2009
译者:西柚,2023

塔罗牌:普通人的手势语
仪态就是含义。
向左是回忆,向右是未来。
那些直视你的人看到的是现在。
用注意力填满你的头脑。
做图像所做的,而不是它们所说的。
被动消极地坐着,接受地站着,主动积极地走着。
体现你的目的地。
用剑决斗,用杖建造,
提供一个杯子,给予一枚硬币。
让手来表现你的意图。
忘记红色是什么,并注意什么是红色的,
坚持主张一个数字就像你世界里的希望灯塔,
脱下你的盔甲;
因为把黄金变成铅的东西也会把盐变成糖,
因为一步实现的东西,另一步可能会妨碍,
还因为你穿的衣服会让你筋疲力尽。
通过它的朋友了解一个形象:
最深刻的真理隐藏在明显的地方。
仪态就是含义。
代表着体现的概念本身。塔罗牌的每张图像都有一个主角,而这个主角有一个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身体镜像的身体。牌中的人物存在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一个直接的建议:“要像我一样!用你自己的双脚站直,记住你从哪里来,练习你的手艺,尊重你的才能”。读牌者说出这样的话,会在客户的大脑中引起从“做”到“存在”的隐喻映射。请记住,当前认知科学的主要发现之一是,思想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我们通过记忆、连接、推理和感觉运动反应,而不自觉地意识到它。我们根本无法不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读牌者只需描述牌中所描述的动作,就能让客户的大脑中出现这个过程。这里的主要假设是,鉴于这些图像在关于该人的读牌中被描述的背景,客户的大脑会自然地将该人物所做的任何事情映射为关于如何行为的取向。更准确地说,从牌上描述的字面态度将被客户的大脑映射成一种隐喻的存在方式。没有什么“技巧”,也没有什么神奇的词语。对一个形象的描述也没有对错之分。我们真正想要的是让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解释”摆脱束缚,这样客户就可以在前语言水平上体验图像,我们的语言只是建立在这种体验之上。但当然,我们的大脑不会简单地在字面上处理这些信息。隐喻性思维是从我们对世界的字面体验中产生的。在一个基本的层面上,我们的字面语言说明了我们对物体和事件的直接、具体化的经验,然后我们在此基础上通过赋予所有这些字面体验以隐喻的价值来建立更抽象的交流模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用我们的直接体验来描述那些与我们的“此时此地”没有直接联系的事件。由于所有的隐喻都意味着从源域到目标域的属性转移,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在物理上所知道的东西来理解或描述那些不能在物理上体验到的东西。我已经描述过我们使用空间来映射我们对时间的理解的方式。通过观察一连串的几张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经历的时间流逝的方式。但定义我们对时间的理解的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方位。塔罗牌的每一张图像都描绘了一种运动,隐含着一种时间感。例如,比较一下愚人的稳定速度和高塔的突变动量。审判中的速度是我们在隐士中看不到的,而正义中的平稳节奏是我们在皇帝中可能直觉到的,但与街头艺人相比感觉很慢。这种时间感再次来自于我们对所描述的行为的个人和直接体验,并提出了可用于读牌中的叙事元素。
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些很明显的事情,甚至可能被认为是荒谬的:塔罗牌中每个人物的身份都是由其姿势决定的。愚人肩上背着包,另一只手拿着手杖,被一只狗追着走。如果我们决定表现愚人坐在宝座上,拿着权杖,他就不再是一个愚人了。这些都是赋予“皇帝”视觉身份的属性。形状就是意义,因此,每个人物的姿势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被我们反映出来,可以从多感官的角度来体验。我们可以记住在风景中行走的感觉——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时间被描绘出来——我们可以记住乡间的气味,回忆太阳照在我们背上的温暖感觉,或者回忆被狗追赶的可怕想法。更重要的是,反映这个形象会向我们暗示,我们应该无视那条狗,以稳定的速度行走。在字面或隐喻的层面上,这就是图像所要告诉我们的一切,因为这就是这个行动所能给予我们的一切。
向左是回忆,向右是未来。那些直视你的人看到的是现在。
是在暗指我们的时空坐标:我们通过空间的移动来学习理解时间。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詹森(Mark Johnson)在他们的《体验哲学》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模型来说明这个比喻:
移动观察者隐喻(隐喻的认知机制实际上就是将源领域的经验映射到目标域)
源领域(空间运动):目标域(时间上的变化)
观察者的位置:现在
观察者面前的空间:未来
观察者背后的空间:过去
观察者路径上的位置:时间在运动中
观察者移动的距离:“已经过去的”时间量
这些简单的坐标:左边(观察者背后的空间),中间(观察者的位置),右边(观察者面前的空间)给了我们一些可以看到的东西,一些可以反映的东西,因此,一些可以理解的东西:一种流动感,一个故事情节,一个我们可以定义为“正在发生什么”或“我们要去哪里”的叙述连续体。
目前关于体现意义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在对世界的身体体验的基础上建立我们更抽象的思想,从最基本的方向,如上、下、直、弯、斜、水平和垂直、后退和前进,到我们能够进行的最复杂的心理操作,如数学或哲学探索。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用“直”来形容一个男人时,我们不会认为他有一根铁棍而不是脊柱,当我们用“弯”来形容某个人时,没有人怀疑脊柱侧弯,或者当我们谈论一个女人“冷”时,没有人会考虑用她来储存鱼。我们能够自动将这些属性从我们原来的体验转移到呈现给我们的新环境中。回到塔罗牌,即使从肖像学的角度来看,隐士可以被看作是代表命运的逆转,即老年、时间或禁欲主义的放弃,我们必须首先把它看作是在拐杖和灯笼帮助下行走的男人。一个人可能对禁欲主义一无所知,但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曾在某个时候使用过灯笼。从肖像学——道德/寓言学——的角度知道这张牌的含义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这并不是与客户交谈时更普遍的东西。那都是理论上的信息,客户不一定能与她的个人体验联系起来。但我们都曾用灯笼看过,因此,我们可以用这种体验来理解其他事件,与使用实际的灯笼不同。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当我们向一个人描述“隐士”如何“用他的光来获得清晰”时,这个人不会只是听到我们谈论更换保时捷的前灯泡,而有可能是关于一个需要被理解的问题。约瑟夫·格雷迪(Joseph Grady)把初级隐喻说成是我们从对世界的身体体验中映射出来的那些第一层次的抽象概念。在这些初级隐喻中,我们有“理解是看到”:
理解是看到隐喻
源领域(视觉):目标域(理解)
所看到的对象:想法/概念
清晰地看到一个对象:理解一个想法
看的人:理解的人
光:理性之“光”
视觉焦点:内心关注
视觉敏锐度:内心敏锐度
身体的观看位置:内心观点态度
注意这些映射如何适用于隐士,以及对隐士的态度或姿势的字面描述如何凭借“理解就是看到”的隐喻来理解。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将这些来源映射到这些目标上,而没有过多地注意到这一点。这似乎是抽象思维产生的方式。因此,当我谈到从字面上读牌是激发一个人的体验含义的最直接方式时,我不是请你掰着手指头,相信你的“天赋”和猜测,或试图通过任何狡猾的手段来获得正确的结果,而是理解和利用我们大脑创造含义的方式。下面我复制了一份由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詹森(Mark Johnson)编制的主要隐喻清单。我把一些塔罗牌图像与它们配对。试着想一想,图像的字面描述能引起这些主要隐喻的句子:
爱情是温暖的:太阳
地位高的是大的:教皇、魔鬼、审判
快乐是向上的:审判、街头艺人
微弱的是向下的:倒吊人、高塔
亲密是接近的:太阳、情人
困难是重负:愚人、星星、节制
相似的是接近的:魔鬼、太阳、月亮
线性标尺是路径:杖、剑、杯、币的整个花色
机构是实体结构:高塔
帮助是支持:高塔、战车
时间是运动:命运之轮、隐士、倒吊人
状况是地点:倒吊人、魔鬼、女教皇、命运之轮
变化是运动:命运之轮、死亡
目的是目的地:世界、战车、隐士、愚人
目的是被欲求对象:情人、愚人、世界
原因是物理力量:星星、命运之轮、死亡、高塔、审判
关系是围绕的:情人、太阳、高塔、魔鬼
控制是向上的:倒吊人、正义、力量、皇帝、皇后、高塔、街头艺人
理解是看到:隐士
理解是抓紧:力量、女教皇
看到是触摸:太阳、隐士、高塔
你可能会注意到同样的图像是如何与几个不同的主要隐喻配对的。如果我们用“用他的灯笼看”来谈论隐士,“理解是看见”的隐喻似乎很恰当,但如果我们加上“隐士用他的灯笼看他从哪里来”,那么我们就需要用“时间是运动”的隐喻来映射牌的左边是“过去”,牌的右边是未来,整个左右运动是隐士一生的座标。虽然从字面上看,隐士可能是在视觉上回溯他的脚步,但这句话邀请我们的大脑理解其隐喻意义,即“看过去”。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展我们的读牌,说“隐士用他的灯笼看他从哪里来,了解他要去哪里”,我们将需要“目的是目的地”的隐喻来重新规划隐士的行动,使其成为引导定位的内心活动,成为一个目标。就像一个简单的概念可以被映射到一个单一的身体体验中一样,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几个身体体验——看、走、妥善处理身体障碍——的所有信息为一个更复杂的概念服务。将“理解是看到”的隐喻与“时间是运动”的隐喻和“目的是目的地”的隐喻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看到一个用手杖走路并将灯笼指向左边的男人是让我们的体验赋特征于我们的行动。
用注意力填满你的头脑。
这把钥匙与人物的头部相对应,或者更准确地说,与他们的眼神相对应。通过观察人物的头部,我们会知道这个人物是在暗示我们关注过去(左)、现在(直视)还是未来(右)。根据主角头部的方向,一张牌会对我们说“回头看”、“向前看”、“关注这里和现在”;但当我们在一个牌串中看到不止一张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头部运动”,描述注意力的改变、重新定向甚至是持续。
做图像所做的,而不是它们所说的。
是观察人物行动的直接暗示,不会被其所谓的象征含义所干扰。例如,在月亮这张牌中,我曾提出,没有人类人物表明我们身体的缺失。这比把月亮看作“母亲的原型”要有用得多。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夜晚是黑暗的,我们有一系列的体验性学习,将黑暗与危险联系起来。但我们也有关于月亮的体验,给我们一种时间感:我们知道黑暗只会持续两星期,而在月亮牌之后,我们有太阳牌,这一点得到了加强:白天胜过夜晚。不过,就其本身而言,我们还是可以把月亮看成是满月,并把我们所有关于这一事件每月发生一次的体验看成是满月。在这里,对图像本身的现象学观察正在暗示一种不同的时间感,我们可以通过将我们的字面体验转移到一个隐喻中,映射成一个女性的周期,如果这在类比上是合理的。月亮不是一个无实体的、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我们都经历过的事件。我们不需要阅读克莱丽莎·平蔻拉·埃思戴丝(Clarissa Pinkola-Este)的书来理解月亮的含义,我们只需要一扇窗。
被动消极地坐着,接受地站着,主动积极地走着。体现你的目的地。
杰罗姆·费尔德曼(Jerome Feldman)在他的非凡著作《从分子到隐喻》中指出:“……通过体现模拟的理解过程本质上涉及到一个视角的选择。三个基本的选择是:施事者(推动)、体验者(被推动)和观察者(看到的第三方)”。“反映塔罗牌”的很大一部分意思是与在牌中找到我们自己有关。我们在塔罗牌中发现三种主要的身体姿势:坐、站和走。我们拥有这三种状态的体验信息。坐着是我们最被动的状态,仅次于躺着(塔罗牌中没有描绘)。就像学习站立的孩子一样,在直立的状态下我们成为“对象中的一个对象”。我们与周围的环境接触,但我们还不活跃。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种状态描述为“接受地”。我们收集信息,我们发出信号,但没有明确的运动感。这种运动将是下一个步骤,被定义为行走的实际行动。(塔罗牌中还有其他身体姿势的定义,如高塔中的坠落和星星中的跪下。这两种姿势都意味着比站着不动更进一步,因此它们将被认为是主动的)。这三个动作中的任何一个都定义了我们思想的“目的地”,我们的身体所表达的态度。反映纸牌就意味着反映这种身体态度,无论是在字面上还是在隐喻的层面上。例如,我们已经看到愚人是如何向前走的,眼睛盯着未来。在字面层面上,这种身体姿态可以通过散步来反映,而在隐喻层面上,我们可以谈论“继续前进”,以此来暗示我们正在忘记一个前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物姿势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被看作是直接的建议,其应用可以是字面的,也可以是隐喻的。比较我们在一排牌中看到的人物的不同身体姿势,给我们一种描述行动演变或变化的连续运动的感觉:从一张显示人物坐下的牌到一张显示人物行走的牌,明确表明要采取行动,而反之则表明我们在等待。在每个层面上:头、身体和手,人物都在给我们提供直接的指示,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或如何行动。
用剑决斗,用杖建造,提供一个杯子,给予一枚硬币。
四种元素符合塔罗牌的花色:剑、杖、杯和硬。我们用手操纵所有这些元素。我们对它们的用途和使用它们的背景都决定了它们的含义。想一想,如果一个骑士挑战另一个骑士进行决斗,而在最后一刻,每个战士都抽出一个杯子而不是一把剑,会发生什么?整个事件将被重新定义,杯子的“交叉”将唤起我们一系列不同的多感官参考,而不是由剑的交叉所唤起的。两个杯子碰在一起的声音,以及它在所有不同感官层面上带来的所有记忆,将是杯花色的含义,就像两把剑相撞的声音,以及这个声音带来的所有场景,将是剑花色的含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让手来表明你的意图”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一个给我们杯子的人和一个用剑指着我们或给我们硬币的人的意图截然不同。牌中人物的手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人物在做什么,由于我们对任何对象的体验都有情感成分,隐含在我们对目标的解读中,这样的对象会暗示我们完成人物用手做的任何事情,并告诉我们这个人物希望实现的是什么。
让手来表现你的意图。
看一张牌,人物的手给了我们具体的想法,让我们知道模仿什么样的动作才有意义。连续看几张牌,手的每个动作都可以被看作是动作序列中的步骤,揭示出一个更复杂和完整的意图。一个角色所持有的对象转变为不同的对象,将暗示我们的目标有相应的演变或重新解释。一个被动的权杖变成了手杖,暗示着行动,就像一个正在倒水的杯子,对称地转变成一个被捆绑的人,暗示着停滞不前。
忘记红色是什么,并注意什么是红色的,
是另一个关于将体验置于非实体的象征主义之上的说法。正是我们对红色的体验,如血液在我们血管中奔流,赋予了红色以含义。由于这一节和下面的五节是对称的,这一行将反映诗中的另一行:因为把黄金变成铅的东西也会把盐变成糖。含义,由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所定义,如果一个金属神只从我们珍惜的另一种金属的金块上投掷小士兵,金块会有什么不同。我们体验到某种白色粉尘是咸的,另一种是甜的。我们知道“盐”的含义,因为我们的味蕾记得那种特殊的体验,并能将其与“糖”的相关体验区分开来。
坚持主张一个数字就像你世界里的希望灯塔,
与一步实现的东西另一步可能会妨碍有对称性,都是指按顺序使用数字,而不是象征性地使用数字。我们通过手指学习体验数字,并使用这种体现的知识来计数。计数既可以是一个定量的行为,也可以是一个定性的行为。二比一多,这可能意味着二定义了比一更高的数量,但也意味着,如果我们打算冒险进入一个未开发的洞穴,二比一更好,或者如果我们得到了最后一块蛋糕,而我们独自在家,一可能比二更好。数字定义了扩张或收缩的进展。在数字序列上“坚持主张”表明,通过在空间中确定方向,数字将指出我们是在前进还是后退,是在“向上”还是“向下”移动。
脱下你的盔甲;
与你穿的衣服会让你筋疲力尽是对称的。这两个句子邀请我们把塔罗牌人物的逐渐裸露解读为通过对物质世界的超越而作为赋权。在王牌的序列中,人物开始时穿得很厚实,一旦天国变得更加存在,角色们就开始脱衣服。这个信息似乎很简单:我们需要穿的越多,我们的力量就越小。我们被我们的地位、社会观念、角色和不安全感所限制。一个赤裸裸的角色成为纯粹的运动。 在世俗的层面上,我会重新规划,说超越在于超越我们对地位象征的琐碎需求,而流动只有在我们放下垂直防御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不能被刺穿的肉体不能被爱。一座凸起的桥是无法跨越的。
通过它的朋友了解一个形象:
是对对称性概念的一种暗示。任何图像在另一个图像上都有一个“朋友”,分享它的一些视觉或概念属性。这些视觉上的配对有些是很明显的,比如情人和审判,或者节制和星星,有些是概念性的,比如教皇和魔鬼,因此更难把握。除此之外,上述一组钥匙表明,所有的头与其他的头都是对称的,所有的身体与其他的身体都是对称的,所有的手,以及他们持有的对象,与其他的手和对象都是对称的。比较和对比这些对称性是我们的叙事方式。但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的东西是对称的,比如女教皇的身体和高塔中的建筑。(通过比较皇冠从一个图像到另一个图像的演变,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战车顶棚的柱子与倒吊人中的树是对称的,太阳中的天体与隐士的灯笼也是对称的。事实上,如果你把牌摊开,让你一下子只看到所有牌的一半,你会发现无数的对称性。它们不是由我来指出的,而是由你来发现的。
所有这些钥匙都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将个别牌作为行动来对待,也可以通过比较这些行动在牌的序列中的演变来得出很多信息。马克·詹森(Mark Johnson)在他的《身体的含义》一书中告诉我们,“生命和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认知科学家谈到“模式”是我们理解体验的概念性结构。我们通过生活体验学到的并已在我们大脑中编码的所有运动模式,在对我们的环境作出反应时被激活。由于我们的大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我调节的最佳匹配寻求机制,这往往发生在我们有意识的认知之下。但是,这些模式所具有的带来记忆、感觉和生理感觉的力量,正是含义创造的行为。我们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事情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经历了它们,不是作为抽象的构造,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马克·詹森(Mark Johnson)还指出,奇怪的是,我们的接合点在感知行为中被抹去了: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而是我们的身体所接触到的这些东西。这使得我们非常容易忽视我们自己的身体性作为含义创造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最深刻的真理隐藏在明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