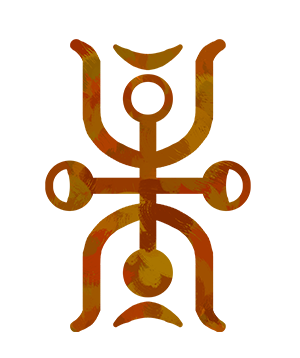记忆药丸
Enrique Enriquez免费分享的博客文章。
本文于2008年在Enrique的个人博客Tarology中发表(此博客现已关闭多年,无法查看)。
恩里克•恩里克斯在文中通过探索图像在中世纪是如何运作的,进而带大家一起探究和思考塔罗牌的视觉语言。
作者:恩里克·恩里克斯,纽约,2008
译者:西柚,2023

记忆药丸
“有一种视觉语言的存在;它是经过考验的;它已经运作了几千年了。这就像,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家,那就有规则;有音符。我认为在艺术中也是如此。比如,你不能在没有意识到美杜莎的情况下用蛇做假发并把它粘在人体模型上。你不可能成功。你不能做到那样。因为在你被告知它的那一刻,它就会完全改变了它。除非你知道它,否则它就不会完成。”
——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srt)
对大多数人来说,塔罗牌的“官方”故事似乎是从安托万·科特·德·格贝林(Antoine Court de Gebelín)开始的,他在1781年在他的百科全书 《原始世界与现代世界进行分析和比较》中发表了一篇关于塔罗牌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些人认为他是第一个认识到塔罗牌是启蒙工具的原因。我们应该感谢科特·德·格贝林的这一见解,只是他的文章也开创了一种与塔罗牌相关的新方式:无论谁设计了解释塔罗牌的理论,都有权重新绘制其图像,使其符合该理论。从那以后,塔罗牌就再也不像以前一样了。事实上,今天的塔罗牌甚至在一整周内都不会保持不变!每当我们眨眼的时候,塔罗牌就会变得不一样。每当我们眨眼的时候,塔罗牌就会遭受另一次残害。它已经变成了编辑想让它变成的任何东西。这个过程的发展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从18世纪开始,它的主要成分是几个连续的作者的自我,到了20世纪,它变成了一套纯粹由经济利益驱动的发明。市场基本上每个月都需要新的东西来销售:“如果我们已经卖出了卡巴拉,还有美人鱼,现在我们可以卖出美人鱼的卡巴拉了。”“有些人喜欢狮子狗,有些人喜欢维也纳,所以,让我们给他们提供维也纳狮子狗的塔罗牌。然后,维也纳人鱼塔罗牌的卡巴拉贵宾犬!”塔罗牌是一个罗夏测试,在18、19和20世纪初,它说的是那些把自己的理论投射到塔罗牌上的人的自我,而不是塔罗牌本身。现在,在21世纪,塔罗牌说的更多的是市场据说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它本身。
我们可以问自己:“在所有这些疯狂之前,还发生了什么?”我们会注意到塔罗牌中的图像与欧洲的罗马式大教堂有着形式上的联系,我们会观察到塔罗牌的主题在整个中世纪文学中也可以找到。只要翻翻中世纪的浪漫、小说、史诗和传奇,就能看到我们在塔罗牌中发现的同样的宇宙。塔罗牌的宫廷牌充满了克雷蒂安·德·特鲁瓦(Chrétien de Troyes)的浪漫曲的精华。我们在纪尧姆·德·洛里斯(Guillaume de Lorris)的《玫瑰的浪漫》原版中找到了太阳的花园的影子,在玛丽·德·法兰西(Marie de France)的《Eliduc》中发现了我们的女教皇。我们可能想在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看到我们的愚人,或者我们可能更愿意在拉蒙·卢尔(Ramón Lull)的《布兰克尔纳》中找到他,以及我们的教皇和隐士。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翻阅中世纪的文学作品,找到像宝剑骑士那样的骑士,像神殿那样的塔楼,像我们的皇帝那样的国王,像星星中的女士那样的女郎,或者像圣杯侍从和他的朋友警棍侍从那样的侍从,等等。
如果我们问自己:“在中世纪,图像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会意识到,在书面文字不足的地方,图像被用来传达含义。我们会注意到,这些图像是以一种连续的方式使用的,一步一步地传递信息,就像大教堂里的十字路口,或者插图手稿的小插图。我们会注意到,这种连续的方式包括许多看似不相干的符号的并置,这些符号放在一起,就会产生寓意。中世纪的寓言旨在以一种读者或听众可以理解的方式来描述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我们的数码世界里,我们会说寓言是一个可能难以理解的过程的“友好界面”。寓言往往赋予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以人的面孔。音乐将被描绘成一个被音乐家的手艺元素所包围的女人。同样地,绘画、爱情、哲学、美德或人类的时代,都成为具有某些独特的象征性属性的人类角色。在塔罗牌中,我们会发现既使用人类角色来描绘一个抽象的概念,又使用符号来赋予这个人类角色以寓言式的身份。比如说,想想正义。正义是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女人。我们怎么知道她是正义,而不是皇后、女教皇或任何一位王后?因为她身上有独特的符号。正义持有一把剑和一把秤。如果我们想一想,只有通过谈论剑、天平、切割、测量和平衡,我们才能领会像“正义”这样的抽象概念。
在探索中世纪的艺术时,我们也会注意到中世纪的寓言是基于背景的。在他的“上帝之城”中,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谈到了“人类之城”和“上帝之城”,前者是有形的、易逝的,后者是空灵的、永恒的。但在他的著作中,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改变了他的隐喻的指称。耶路撒冷,这个地理上的城市,要么与巴比伦对比,被视为上帝之城,要么与它自己对比,或者与新耶路撒冷的田园诗般的想法对比,被视为人类之城。在塔罗牌中,教皇既可以是作为人的教皇,也可以是作为机构的教皇。他可以是教会或我们自己的父亲/神父。根据他周围的牌的排列,教皇可以被看作是给我们祝福,也可以是背弃我们。就像我们在中世纪文学中观察到的那样,教皇的寓意属性可以根据图像出现的环境而改变。延伸一下这个概念,如果我们在高塔(神殿)之前有愚人,我们可以说一个朝圣者正在到达一座塔楼前。但如果我们把牌重新排列,让高塔(神殿)在愚人之前,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朝圣者离开了一座塔楼。这两张牌可以创造两个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具有完全不同寓意的“短语”。同样,放在情人面前的十三号牌可能会显得很危险,但看到十三号牌放在倒吊人面前会给我们一种解脱的感觉。正义在情人旁边可能意味着婚姻,但正义在高塔(神殿)旁边可能被视为离婚。太阳在魔鬼面前意味着监禁,而魔鬼在高塔(神殿)面前则意味着解放,等等。就像耶路撒冷城的形而上学性质被圣奥古斯丁重新定义一样,任何塔罗牌图像的寓意都会根据与之配对的图像而改变。并置重新定义了含义。
最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中世纪的图像,无论是图像还是文学,都是在对称的理念下运作的:每个符号都是一种呼唤,由其他符号来回应。当我们探讨这个想法时,我们发现它源于对《圣经》的理解方式:《新约》中的每个场景都被认为与《旧约》中的一个场景“对称”。四位先知与四位福音书作者相对应,甘露从天而降与耶稣增产面包相对应。上帝决定牺牲他的儿子,与亚伯拉罕决定牺牲他的儿子的方式相同,等等。我们看到这种想法是如何被带入文学和艺术的,因此一切都通过形式上或概念上的共鸣与其他事物相关。例如,想想但丁的喜剧,它告诉我们,所有的惩罚都符合激发它们的罪恶,而所有的奖励都符合它们打算表彰的美德。这种对称性不仅渗透到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而且也参与到塔罗牌中的符号传达给我们的方式中,以及我们如何看待它们的相关性。说十字架上的木头来自承载原罪的苹果树,就像中世纪所说的那样,与说太阳中人物背后的墙隐藏着审判中的场景,或街头艺人的包和愚人的包是同一个,或正义脖子上挂着用来挂倒吊人的绳子,没有什么不同。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即使它是作为一种机会游戏被创造出来的,塔罗牌也有一种基于中世纪使用图像方式的内在语言。我们不需要深入研究神秘学,也不需要发明什么新东西。我们只需要了解图像是如何工作的,以及我们如何通过图像“工作”。很难说塔罗牌的图像只是用来玩的有趣的图像。但是如果不被图像“玩弄”,就不能玩弄图像,因为我们的思想是可塑的。当我们把我们的想法灌输给一个图像,而这个图像体现了这些想法,我们的想法就会改变。当一个图像容纳了我们的思想,它就重新塑造了它们。这就是图像如何改变我们。我们不需要证明创造塔罗牌的人的一厢情愿的奥秘意图。即使它只是为了游戏而构思的,塔罗牌作为洞察力工具的可能性也是建立在其意象性质的核心中的。如果我们看这些图像,很可能会有一瞬间的非语言洞察力。我们将通过寓言式的思考,用一种通过概念并置、视觉韵律和符号的共鸣来表达的语言来做到这一点。这样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玩tarocchi 的人会觉得倾向于在牌中找到自己,也会玩一种叫“tarocchi appropriate”的东西,我们会理解马泰奥·马里亚·博亚尔多(Mateo María Boiardo)或特奥菲洛·弗伦戈(Teófilo Filengo)的诗,都是基于塔罗牌中图像的内在叙事性。
鉴于塔罗牌图像可以与之联系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说塔罗牌本身就带有被解读的概念。
当我们按照这些中世纪的观念探索塔罗牌时,我们注意到对称的观念是如何贯穿始终的。1号牌中的人物和21号牌中的人物是对称的。2号牌的人物和20号牌的人物是相互补充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3号牌和19号牌之间,或者4号牌和18号牌之间,或者愚人和13号牌之间。马赛塔罗牌中表达这种对称思想的例子非常多,不可能全部指出来。皇后上的鸟可以在皇帝、星星和世界中找到。世界中的狮子可以在力量中找到,但它也与抓挠愚人背后的生物对称。正义的剑与宝剑Ace对称,硬币Ace与街头艺人右手上的硬币对称。节制的罐子与星星的罐子和整个圣杯牌组是对称的。命运之轮站在星星倒水的那条河上,轮子顶端的冠状物与我们看到的驾驶战车的人物相同。皇帝、倒吊人和世界都有相同的腿部姿态。马赛塔罗牌是建立在无限的对称性上。我们注意到马赛塔罗牌中的所有元素都与其他元素有关,世界中的曼陀罗与宝剑牌组中的弯刀形成的结构产生了共鸣,与魔鬼中的两个人物绑在一起的绳子产生了共鸣,与承载审判天使的云产生了共鸣。 所以,我们在许多其他牌中看到每张牌的一个部分,我们也看到牌中的人物互相影响或互相忽视。当我们看塔罗牌时,我们以直接、自发的方式理解它的人物的姿态。然后,我们寻找一个图像中的手势和符号与另一个或多个图像中的手势和符号镜像的方式。这种动态要求我们承认这些图像的主要特征:塔罗牌用手势说话。我们可以看到塔罗牌中的每一个图像都在赞美一种我们作为人类可以向往的属性。像皇帝这样的图像会赞美“有尊严地坚持”。像倒吊人这样的图像会赞美“忍受我们的命运”,等等。如果我们记住,像中世纪的图像一样,塔罗牌通过使用可以被隐喻的文字姿势来说明非常具体的行动,那么这种概念就触及了塔罗牌一直在给我们的现象学建议。
塔罗牌图像的几个属性是由这种语言提供的。当我们看到太阳中的人物如何触摸对方的心脏和喉咙,我们理解了“发自内心说话”的隐含指示,我们正在解码这种手势语言。当我们注意到街头艺人的桌子少了一条腿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是在说基于物质稳定的生活总是不完整的。同样的语言告诉我们,皇帝的统治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用左手拿着他的权杖;如果我们看一下隐士,我们就会知道,遵循我们的确定性将使我们总是反向走。
遵循这种方法,我们发现了一种语言,塔罗牌不仅会说话,而且告诉我们如何“听”它,或者说我们应该听什么。我们不是简单地在牌中看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是它们坚持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坚持使某些符号活跃起来,而使牌中的其他符号不活跃。在世界旁边的宝剑4,我们被邀请关注由曼陀罗创造的椭圆,并在四把黑色弯刀中重复,因为它们是押韵的。这个韵律暗示着花的元素变冷,并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它们的押韵也让我们看到了宝剑4四角的四个元素和世界四角的四个人物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宝剑4中间的花和世界中心的女人之间的相似性。但是“世界+宝剑4”将不同于“宝剑4+世界”,因为花看起来很脆弱,而女人看起来很有光芒,因此从光芒到脆弱与从脆弱到光芒是不一样的。(我们立即意识到,像“脆弱”或“光芒”这样的词是来自视觉语言的口头翻译,因此只能被视为临时性的词)。但是,如果我们用世界旁边的星星代替宝剑4,我们会注意到,椭圆不再强加给我们。那个椭圆变得不活跃,而女人的姿态变得活跃。从一个跪着的女人过渡到一个跳舞的女人本身就是一个信息,这与我们从一个跳舞的女人到一个跪着的女人所观察到的信息不同。
当我们观察所有这些事情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中世纪的文件,无论其起源或性质如何,都有传达精神真理的唯一意图。当我们从塔罗牌中得到启示时,我们意识到它的符号和中世纪的任何艺术作品的符号一样,都是为了揭示更高的现实。一切都是寓言式的。在那个时代,甚至自然也被看作是《圣经》的寓言。但我们可以怀疑,在中世纪的西欧,这样一个更高的现实将其意象借给了基督教。这并不是说,从我们当代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本身就是那个更高的现实。塔罗牌中的图像是西方人的共同想象基础,其真理超越了基督教。我们说的不是异教徒或新柏拉图式的理解,而是我们已经学会识别为原型的原始心理理解,从扩展的角度看,可以与恩斯特·汉斯·约瑟夫·贡布里希(Ernst H. Gombrich)描述的“对原始的偏爱”相联系。当我们看马赛塔罗牌时,即使没有算命师或任何其他解释者的干扰,我们也能找到确定性。这些图像有一种舒缓的品质,其基础在于它们的简单性、标志性和真实性。所有这些都是将塔罗牌与中世纪的艺术和文学联系起来的属性。我们永远不会第一次看马赛塔罗牌。即使我们能够回忆起我们第一次有意识地看塔罗牌包的时刻,那第一次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些图像:它们并不是新的。我们只是重新遇到了它们。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些图像,因为它们描绘了西方人心理的基础。当我们在看这些剑、这些花、这些杯子、翅膀、动物和塔罗牌中的所有这些人时,实际上是通过类比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如何做人,或成为什么样的人,以便我们能面对生活中的所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