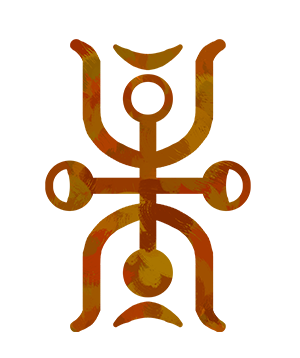马赛会谈|恩里克•恩里克斯
Patrick Smit免费分享的他采访Enrique Enriquez的内容。
本文于2020年1月28日由帕特里克·斯米特在Facebook上的TdM(Tarot de Marseille)小组中发表(帕特里克·斯米特为该小组的前管理员)。
“每当我们谈到鹦鹉和鸽子时,我们就更接近于忘记圆和方之间的区别,而这正是行动的全部意义。”——恩里克•恩里克斯
除了阅读西柚的译文外,你也可以在Facebook上的TdM(Tarot de Marseille)小组中免费查看本篇译文的原文。

马赛会谈|恩里克•恩里克斯
“每当我们谈到鹦鹉和鸽子时,我们就更接近于忘记圆和方之间的区别,而这正是行动的全部意义。”
——恩里克•恩里克斯

Enrique Enriquez,1969年出生,现居美国纽约,委内瑞拉著名塔罗占卜师和现代诗人
Patrick Smit:
很高兴与你分享我对恩里克·恩里克斯的采访。总是很高兴与他交谈,谈论这些我们都喜欢的小艺术作品。谢谢恩里克·恩里克斯,感谢你抽出时间。(最后三个问题是来自该小组的其他三位成员,卡洛斯·安德拉德, 塞尔吉奥·普雷齐奥索和丹·赫什)。阅读愉快!

Patrick Smit:
从亚瑟·爱德华·韦特(和皮克斯·史密斯)的塔罗牌面世的那一刻起,它就主宰了塔罗牌世界,直到今天也是如此,还有它的衍生品。马赛塔罗牌似乎只获得了少数的爱好者,法国是个例外。但如今,有纸牌制造商专注于马赛塔罗牌,Flornoy、Hismans、Robledo、Renault,越来越多的书以英语出版,包括你的书、卡梅利亚·埃利亚斯的书和本-多夫的书等。你如何解释当前马赛塔罗牌的复兴?
Enrique Enriquez:
可以肯定地说,对古代事物的信仰几乎总是回应着对现在的失望。当代塔罗牌的图像是如此平淡,以至于我们不可避免地喜欢上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想象中更接近某种最初火花的图像。
然而,我们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塔罗牌世界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而是一个市场。与其说是知识的交流,不如说是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可能很多人对马赛塔罗牌和任何其他古老的塔罗牌的兴趣,更多的是与收集饰品的兴奋刺激有关,而不是对这些图像的真正投资。

Patrick Smit:
你能说说“鸟语”以及它与马赛塔罗牌的联系吗?
Enrique Enriquez:
鸟语产生于语言分解成形式的地方。这其中有一部分与同音异义有关,因此位于马赛塔罗牌的王牌名称中。这还只是一个起点。一个更广泛的观点会让我们理解,那一系列图像的结构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视觉节奏上的,其中某些模式会重复。看清节奏而不被图像中的轶事所干扰,将诗歌置于虚构的东西之上,这样我们就能与世界的脉搏同步并与时间融合,这就是鸟语的意义所在。
鸟语的想法与回归天堂有关,也就是说,回归到一个理想状态。回到一切事物背后的原始节奏,意味着放弃我们对事物具体含义的依恋。它不是关于破译象征符号,而是关于阅读模式,并理解没有含义的东西仍然有意义。

Patrick Smit:
你的教义似乎与查莱·昂格尔的教义有重叠,她的影响很大,但没有多少人熟悉她。你是否受到她的影响,如果是的话,是以什么方式?
Enrique Enriquez:
查莱·昂格尔的书是唯一一本我可以说是为我开辟了一条道路的书。她教我爱图像胜过爱自己。我记得我是在加拉加斯的一家神秘的书店里发现这本书的。店员不想把它卖给我,或者更确切地说,她坚持认为我更喜欢买有彩色插图的书,而不是这本用廉价纸张印刷的丑陋的小书,她认为这本书不讨人喜欢。
我愿意认为,我只在一个意义上成功地超过了昂格尔。在她的书的结尾,她要求我们把它扔掉。她让我想起了西班牙神秘主义者米格尔·德·莫利诺斯,他写道:“每当到达终点时,工具就会停止,到达港口时,航行就会停止。”(“当一个人到达终点时,工具总是停止的。当一个人到达港口时,导航也是如此。”)。就像查莱·昂格尔敦促我们一旦内化了她的书的信息就把它扔进垃圾桶一样,我想说,一旦塔罗牌图像之间的空间所包含的诗意结构占据了我们,我们必须把塔罗牌扔掉。
Patrick Smit:
在你的教义中,你谈到了纸牌讲述的故事中的“类比”和“押韵”,你能解释一下你的意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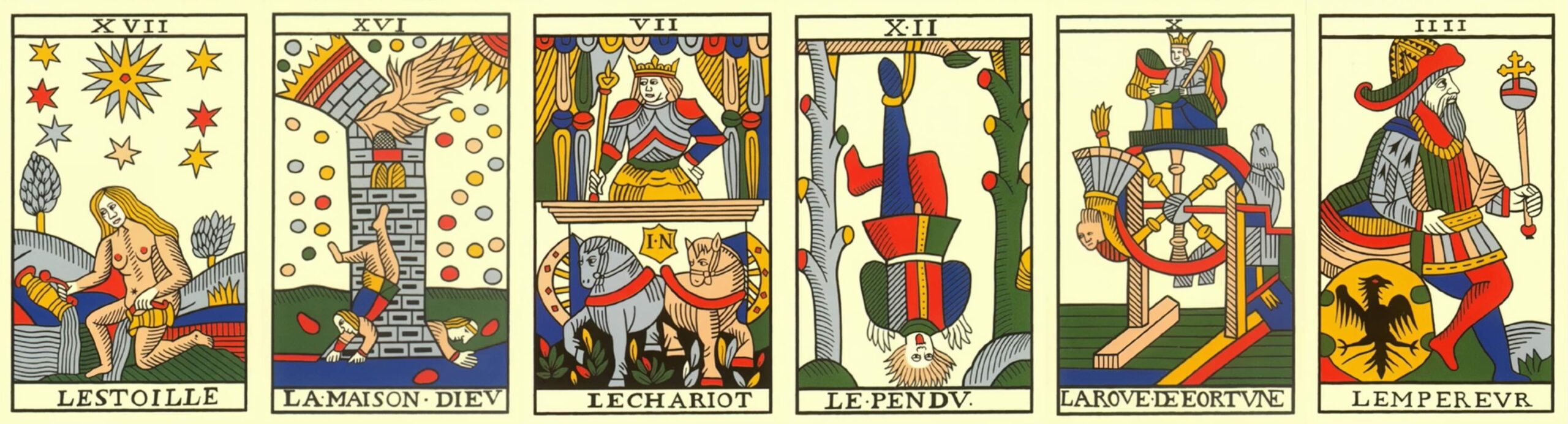
Enrique Enriquez:
马赛塔罗牌可以作为一个反复出现的梦融入想象中。对我来说,它总是从一个裸体女人把水倒进溪流开始。喷出的水突然变成两个从燃烧的建筑物中掉下来的人。那些人是拉车的马,但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看起来像柱子,一个人倒挂在柱子上,这个人在交叉双腿时,成为坐在摩天轮上的一个皇帝。这个梦有无穷无尽的化身。每一个都包含所有其他的。回顾它,我们得到了品味形式的真理的可能性。到那时,回到米格尔·德·莫利诺斯的话,我们可以从桌子上站起来,把牌留在身后,让世界对我们说话。

Patrick Smit:
我知道你经常使用弗洛诺伊的诺布莱特牌(1650 Jean Noblet),你能告诉我是什么让它如此特别吗?
Enrique Enriquez:
诺布莱特的塔罗牌更小,更容易洗牌,但也更容易摊在桌上。记住,我最喜欢和人一起看塔罗牌的地方是咖啡馆。但我认为自从那副塔罗牌送给我后,我就把它放在口袋里,最重要的原因是让·克劳德和罗克珊有手工制作它们的讲究,遵循那些塔罗牌第一次印刷时的流程。在这方面,我的诺布莱特牌是一个原件。我一直认为塔罗牌是一套美丽的图像,应该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来进行管理。因此,我一直认为,无论谁和我一起看塔罗牌,都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这样做。让他们有机会看纯正的、真实的、不通过任何机械手段复制的原始图像——最真实的红色、最真实的黄色、最真实的蓝色——似乎一直是一种体面的姿态。毕竟,我不相信塔罗牌的效果来自它的预测能力,也不相信来自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心理预测的投射,它不是来自我们的语言,而是来自图像的存在,来自它们本身的美,以及来自其结构的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世界上一致性的承诺。
Patrick Smit:
你是否有任何与塔罗牌有关的项目,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进行?

Enrique Enriquez:
我教人看塔罗牌,通过私人通信,一对一,采取监督实践的形式。我的日常通信对我来说很珍贵。如果有人联系我,他们可以肯定我会回答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喜欢认为塔罗牌仍然可以是极少数通过口述传统传播的知识形式之一。正因为我非常感谢塔罗牌给我的生活带来的一切,所以我努力报答它,避免出版更多的说教材料而使它变得微不足道。除此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模仿鸟的声音,并在人们的梦中拜访他们。这两项活动都是为我提供实现我最大野心的媒介,也就是让我自己产生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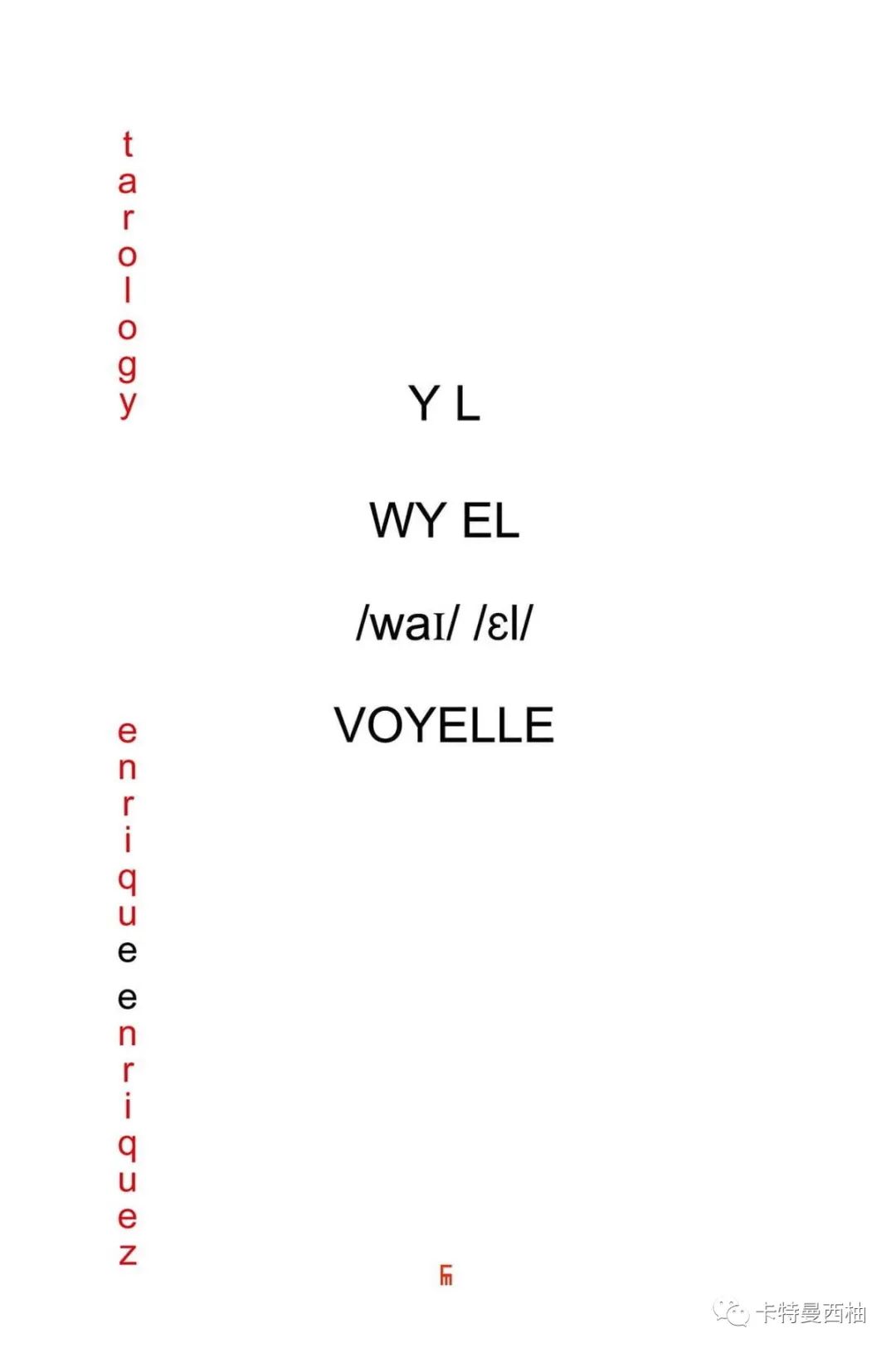
Carlos Andrade:
你会不会考虑将你的“塔罗学”的可能性扩展到普遍的纸牌卜卦上;考虑将你在这方面探索意大利传统的丰富见解作为马赛塔罗牌的基础和依据?
Enrique Enriquez:
多年来,我一直将同样的原则应用于字母表,对我来说,字母表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最伟大的图像系统,因为它体现了我们的两个基本的虚构的东西,圆和方。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把我在工作中形成的想法应用于其他事物。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项工作,那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语言。这意味着调整他人的语言以适应我们自己的需要,不仅仅是通过借用它,而是通过改造它。

Sergio Prezioso:
我知道本-多夫改变了面部表情以表现更多的现代特征。但我想知道这些古老的塔罗牌(例如诺布莱特)是否是按原样绘制的,出于某种原因(P:你认为这种更改是否受到反对/“亵渎”?)
Enrique Enriquez: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300年前的纸牌制作者没有什么浪漫的想象。我认为是那些设法以制作当时流行的产品为生的人。流行的意思是指被公众所了解,但也是指保持可用性。请记住,所有这些扑克牌在人们玩完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如果让·诺布莱特有杜雷罗的精湛技艺,他就不会做塔罗牌了。事实上,我认为今天我们发现这些有点粗糙、笨拙的图像的迷人之处,部分原因正是来自起草这些图像的人的笨拙粗陋。这些是不完美的图像,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看到的原件的副本的廉价拷贝。我们不知道谁第一次看到这些图像,不是睁着眼睛而是闭着眼睛。来到我们面前的是以讹传讹游戏中的最后回声。
当谈到塔罗牌时,我们不能谈论亵渎的事情。我们的整个事业是建立在错误之上的。我们玩的游戏是一种误读。自从安托万·科特·德·杰柏林发表关于塔罗牌的文章以来,情况就是这样,他的文章使我们脱轨,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局面。作为一个类似的例子,我想到了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关于汉字诗学的文章。在埃兹拉·庞德的支持下,这篇文章成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有影响力的灵感来源,即使它已经被完全推翻。费诺洛萨被误导的事实并不影响他的作品所激发的诗歌。塔罗牌作为一种神谕没有真正的血统,这一事实使它变得真正重要,因为它表明,正是我们给一切事物赋予了含义。那么塔罗牌的实践就成了对我们赋予惰性事物价值的能力的伟大庆祝。
在占卜中坚持严格的规则是一个时代的遗留问题,当时读牌被看作是一种咒语,有明确的预言事件的目的。我可以看到这对业余爱好者的吸引力。遵循秘诀,与他人分享,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消磨时间的方式。
Dan Hersh:
为什么你不再读点数牌了,为什么只用三张王牌?

Enrique Enriquez:
事实上,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从来不读点数牌。用完整的塔罗牌解读是英语世界的一种迷信。在欧洲,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只读王牌。
我断然拒绝的是根植于普通家庭主妇的想法,即马赛塔罗牌的小阿卡纳没有图解,或者说它们不能被解读。这些点数牌就像一个花园,我们坐在里面体验世界的韵律节奏。整个塔罗牌体验的目的是使时间加速。事实上,我们可以坐在花园里等待,看生命在世界说的不断转变的语言中,随着事物的升温和降温而繁荣和凋零。但我们不喜欢等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创造了一种人为的情况,即使一个果实可以无缘无故地出现成熟。当我意识到等待的行为本身就是最伟大的神谕时,我倾向于怀疑任何需要一个立即的答案的人是在问错误的问题。
话说回来,不应该有什么教条。我只是寻找一个我认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用点数牌或不用点数牌,都要看你觉得什么是美。我们可以只读偶数的牌,或者名字与问卜者名字押韵的牌,或者我们可以尝试N+7的乌力波的方法,其中每当有牌出现时,我们就忽略它,再数七张牌,选择那张牌代替,我们的读牌也会同样有效。
三张王牌足以产生一个具体的、令人难忘的想法,对方可以把它放进口袋里带回家。这不正是行动的全部意义吗?比起一串三张牌,唯一的改进是根本不用牌。